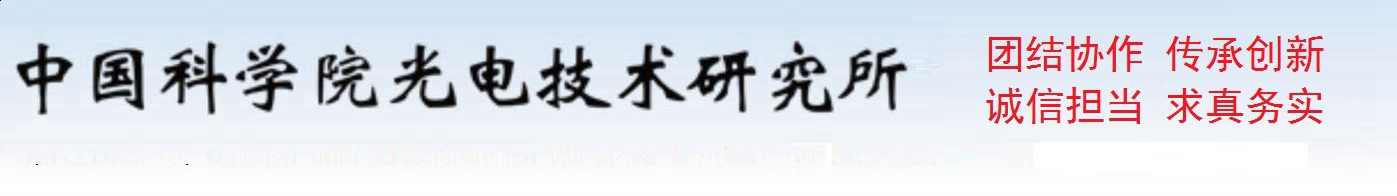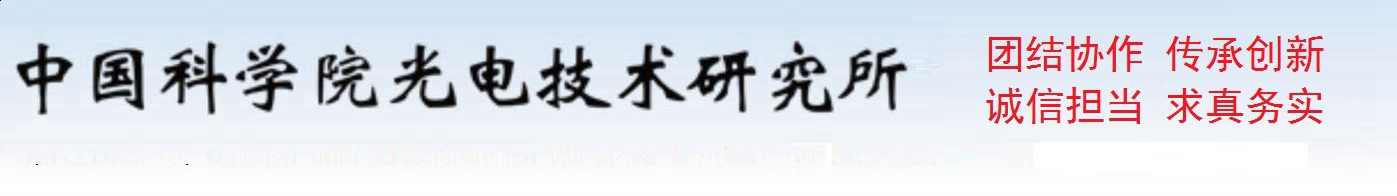若以人生百年划分春夏秋冬,我人生的春季已近尾末。来不及在镜子前端详,认认真真瞧瞧自己的变化,以为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模样。我常常在梦醒时觉着自己还是躺在母亲怀里的孩子,但手不经意地在面庞抚过时,刺手的胡茬让我惊悸,我知道记忆中的日子早已远去不回。当叔叔两字的标签常贴在自个儿身上已不觉别扭,当一直做着的梦成为了现实,当又一个空白的夜里觑见自己渐渐退温的心时,在一阵慌乱中觉得还应该做些什么。
五年前汶川地震我19岁,正在川大课堂上课,我箭步如飞冲出教室,心有余悸在校园走荡。五年后雅安地震我24岁,正躺在研究生的暖床上做白日梦,摇醒后我端坐床头,仰面瞧着天花板坐等地震平息,10秒过去越摇越厉害,20秒时意识到这不再是熟悉的汶川余震,25秒时想要采取行动,不过30秒钟时地震都已过去,心有余悸我赶在回家的路上。箭步如飞的19岁和端坐床头的24岁中间横亘了五年的人和事,还有时间,我正年轻却正在老去。五年前我还热衷于各种励志书籍和演讲,英语也要学李阳的励志英语,那时满脑都是自己成功后光鲜的形象,我无数次幻想自己在成功后,站在聚光灯下的演讲台上像陈安之、李阳、牛根生、俞敏洪等侃侃而谈自己的成功经验。我常常迎着日出站在教学楼顶,高声诵读《I have a dream》,读得自己热血澎湃,我仿佛看到了我万人之上的光茫。五年后虽然还很怀念打鸡血的日子,但它已经不能给我足够的给养。一年前李阳传出家暴,曾经听着入睡的KIM老师甜美的声音变成了电视上的哭诉声,而李阳老师还在全国劳苦奔波,为了他想让三亿中国人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梦想。
记得在《看见》节目的最后,柴静问李阳:“那你认为你是需要帮助的人吗?”他眼神黯然但坚决地说:“我肯定需要帮助。”在四年前想让亿万中国人喝上牛奶的牛根生工厂里传出了三聚氰胺,之后我再也没听到过也再未关注过牛根生讲他的创业故事了。两年前认识了“打假斗士”方舟子通过他的《新语丝》我闻到了象牙塔里的腐臭味,对教育权威们崇敬之心开始动摇,原来象牙塔锁住的仅仅是我们这一群幼象。还是在两年前我发现在我出生那年多出了一个特别的日子五月三十五号,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的出生与那个特别的日子有些许联系,因为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生的意义,这一发现让我有些茫然的兴奋。不久,在网上关注到罗永浩,看过他的演讲视频后他那无比邪门儿的人生让人羡慕更是让人打鸡血,但这次的鸡血和以往的味道不同,它很真实,作用时间更长。他愤然地谈到了郭敬明抄袭案,聊到了什么字会的管理混乱,教育培训行业的内幕,消费者权益…他试图用他熊样的身体改变这世界。之后没想到的是在微博上舟子和老罗这两个在我眼中绝对的正面人物在微博上打起来了,在这众人围观空前热闹的网架中,很难厘清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以致后来有人专门进行了调研总结。我记得的是在这事件中出现了很多人---方舟子,罗永浩,韩寒,柴静,刘菊花,彭律师…我们像猜测艳门照中下一个女主角是谁一样期待着在这个事件中下一个人物的登场,这场戏看得真过瘾。突然我意识到他们都只是生活在远方的戏子,我过着自己的生活看着他们的戏。能够这样一直做个看客也未尝不好,但五年前我有爸妈养着,现在我得考虑自己的活计了。
方罗之战平息了,老罗也去做手机实现自己的梦想去了,我摇摇晃晃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又一分岔口。在汶川地震后五年里自己的价值观遭受着不同等级的余震,新砌好的墙一次次崩塌,又一次次重新糊好,直到又一次强震所有的又崩塌下来。其实只有几匹砖的墙永远成不了房,它没有地基没有结构,说倒就倒。定睛看看这个时代已经走得很邪乎的快,自己的思维速度早赶不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在各种压力和无压力面前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也不清楚何去何从,在这个时代里我没有归宿感。想来想去,也许我的归宿在我的记忆里。但记忆会剥落,人会老去,今天终也会成为记忆。
年轻时有很多冲动,想做很多事,但也许终究只是想想。时隔多年,这些冲动可能会显得弥足珍贵美好,先以此篇记下我曾想写的冲动。